每月一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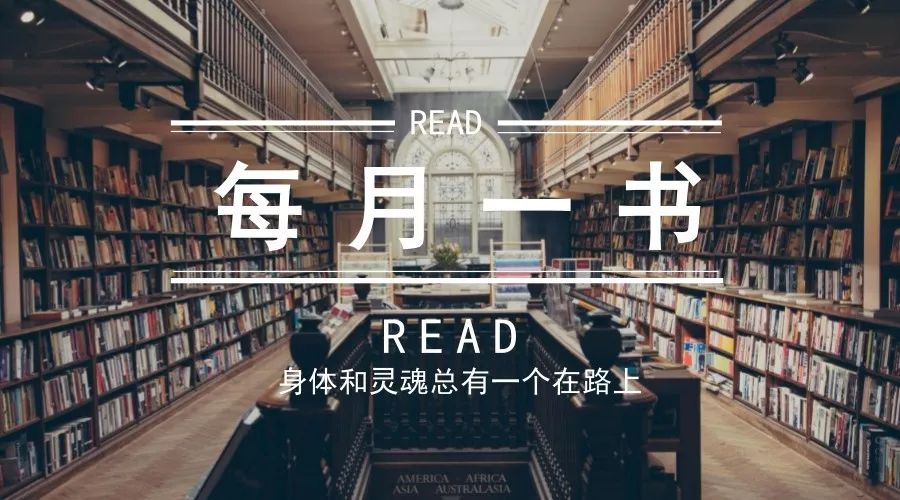
2020年4月
带上一份安静淡雅,探寻世间美妙之物。
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我在阅读她极端的童年故事时,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活。这本书每个人都会喜欢。它甚至比你听说的还要好。
它不是一本励志书,也没有可口的鸡汤。
它是一本自传,是一个女孩对自己成长过程的回忆与思考,是与原生家庭的剥离,更是自我的重新塑造,以及引出的关于教育的意义的思考。
它的动人之处在于,女孩经历了原生家庭给与的苦难,通过教育最终剥离了原生家庭,进行自我创造,她鼓起勇气去打开了生命的无限可能。同时,她并不认为给她无尽苦难的家庭一文不值而毫不留情地将之抛弃,她原谅和接纳父母的不完美。
在“原生家庭”这个议题上,她提供了一份勇敢的答案,值得我们每个或多或少有些怨恨“父母皆祸害”,又不知道怎么“化害为爱”的人,去借鉴和体会。它让我们反思教育的意义,接受教育,但不要让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我们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我们应该多听,少说。我们应该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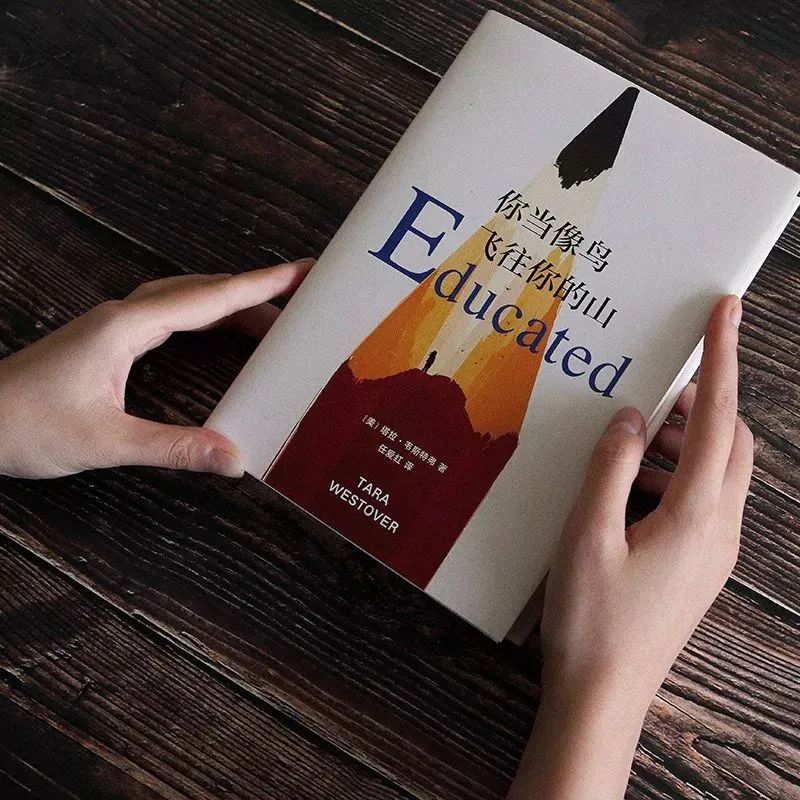
每个原生家庭都会给孩子两样东西,一是常识,它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认识,二是亲情,它是我们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纽带。有些原生家庭给与孩子的这两样东西是礼物和成全,然而有些原生家庭给与的却是刺痛和束缚。那些刺痛和束缚,有些人背负了一辈子,有些人则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痛苦的挣脱和和解。
塔拉属于后者。
塔拉的家在闭塞的大山中,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他们家并不贫穷,然而孩子都在家里出生,没有办出生证明,不上学,生病受伤了也不可以去医院,用自己制作的草药涂抹并等待自愈……
父亲经营一座垃圾废料场,母亲是草药师兼助产士。从小她就在父亲的废料场帮忙干活,或是跟随母亲制作酊剂和精油。他们与世隔绝,相信世界末日终将到来,每天都在囤积物资,做生存准备。
父母给每个孩子设定的未来明确而清晰,男孩接替父亲的工作:开挂车,做焊接,拆废料。女孩接替母亲的工作:承担全部家务,研究草药,成为助产士,生儿育女。
“十八九岁时,我会结婚。爸爸将分给我农场的一个角落,我丈夫会在那里盖间房子。母亲会教我草药和助产的知识。我生孩子时,母亲会来接生。我猜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我不知道未来哪里有大学的影子。”
她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她未曾见过光明。
幸运的是,塔拉见过光明。
随着塔拉步入青春期,父辈主张的不容置疑的声音开始在她心中动摇。父亲不顾她的安危,一次次将她推向咆哮着的几乎要将人脑袋咬下来的轧钢剪刀;一个哥哥屡屡出现暴力倾向,把她的头按进马桶,掐住她的脖子叫她妓女;母亲无视她所受的委屈而选择沉默……
家的形象变了。家庭所谓的忠诚信条,成了围困她的牢笼。
她的另一个哥哥通过自学离家上了大学,为她播下一颗好奇的种子:家之外是否有一个可以救赎她的不同的世界?当她拆下散热器上的铜,将第五百块钢扔进分类箱时,属于她自己的声音渐渐苏醒:离开家,去上学。
在替父亲工作的间歇偷偷自学,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几个月的努力之后,她收获了一个奇迹:大学入学通知书。十七岁,她才第一次走进真正的课堂。
然而,大学是全然陌生的世界。原生家庭的价值观一次次受到挑战,她感觉自己和世界格格不入。
她不知道论文为何物,不明白教科书是用来读的,错认欧洲是一个国家,甚至不认识“大屠杀”这个词,以为犹太人被杀害不过五六个人的规模……她没有朋友,与室友相处艰难。她不明白同居一个屋檐下需要承担家务、如厕后要洗手这样简单的道理,因为她就是被这样教育长大的:洁净是虚伪,污垢才是诚实。
“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说,“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教授抿紧了嘴唇。“谢谢你提了那样一个问题。”说完,他接着讲课。
这节课剩下的时间我几乎一动不敢动。我盯着鞋子,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每当我抬起头,总会有人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我当然是个怪胎,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摆脱无知是一条艰辛的路,塔拉凭借毅力和信念,从不及格生成为全优生。她获得去剑桥大学交换的机会,继而在那里攻读硕士,又成为哈佛大学访学者,最后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然而代价是被视为家庭的背叛者,与父母决裂。分离之痛让她一度发疯,整夜梦魇尖叫,光着脚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梦游狂奔。
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如何追逐自我?自我意愿与家庭责任之间要怎样平衡?……通过写下自己的故事,塔拉找到了一种答案。
借着回忆,塔拉反思了为什么父亲会那么奇怪。她总结出两个原因,是因为信仰摩门教,这种信仰里本身就有一些偏执和极端的观念,不过她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得了躁郁症,放大了他脑海中那些极端偏执的想法。
她依然爱着她的家人,依然在想办法与家人和解。同样,她的家人也爱着她。
你发觉最让人心碎的,正是那些爱的痕迹:父亲为她的唱歌天赋由衷自豪,总是那个坐在剧院第一排最忠实的观众;她去英国上学,父亲首先想到世界末日来了,无法驱车接大洋彼岸的她回家。她带走全部的日记,暗示接下来的离别,父亲给了她一个拥抱,说:
“我爱你,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那从来不是个问题。”
这是我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家庭是我们心中一块难以厘清是非对错的所在,有时它给你温暖,有时它令你刺痛。尽管观念不同,立场相左,爱却始终存在,无法割舍。塔拉在节目上说:
“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不在你的生命中。”
爱的方式也许有缺陷,造成许多伤痛,但塔拉说:
“我已不再是父亲养大的孩子,但他依然是那个养育了我的父亲。”
读这本书,你也许会回望过去,一边感慨着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是多么可怕,一方面又感慨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在以一种笨拙的方式爱着我们。
“孩子最初爱他们父母,等大一些他们评判父母;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原谅父母。”
塔拉最终与自我和解,或者说,重新理解爱与尊重的方式是如此独到。
我想每个读到结尾的人都会惊讶她是以这样的高度处理苦难的,这个方式,与简单的书本教育无关,也与反差生活带来的光环无关。
读读看,因为,你或许也是一只鸟,正在找寻你当飞往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