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连载——苏联解体的能源资本杠杆效应(二)
《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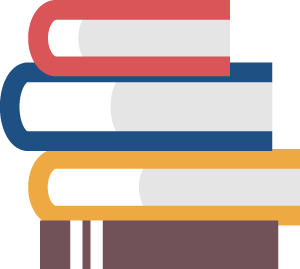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苏联解体的能源资本杠杆效应(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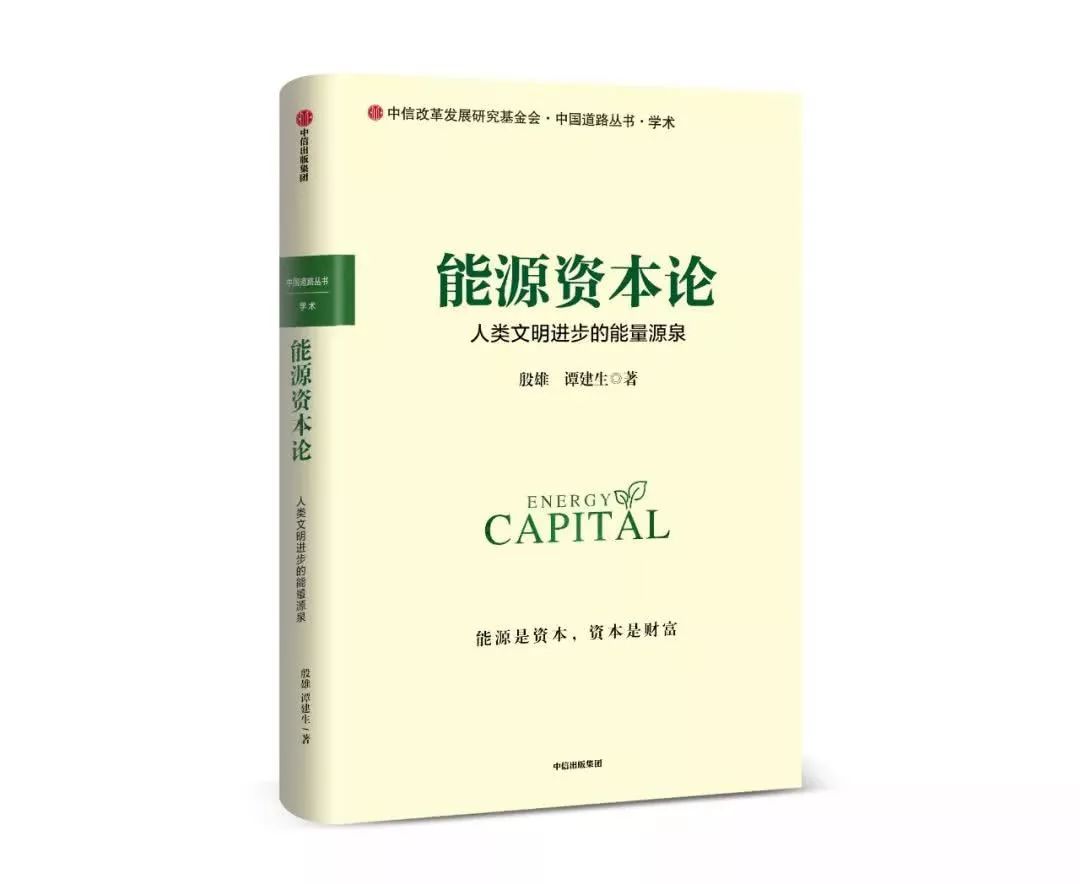
苏联解体的能源资本杠杆效应(二)
殷雄 谭建生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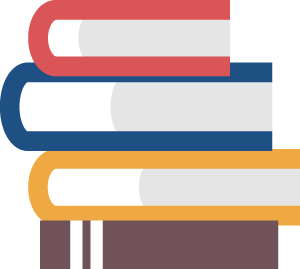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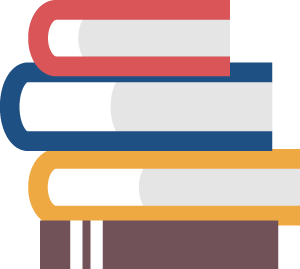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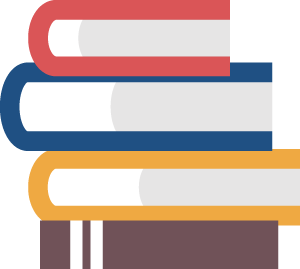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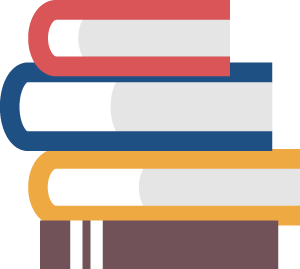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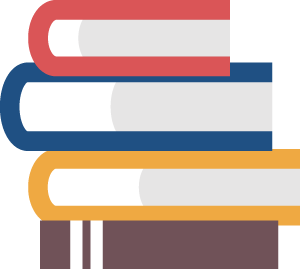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